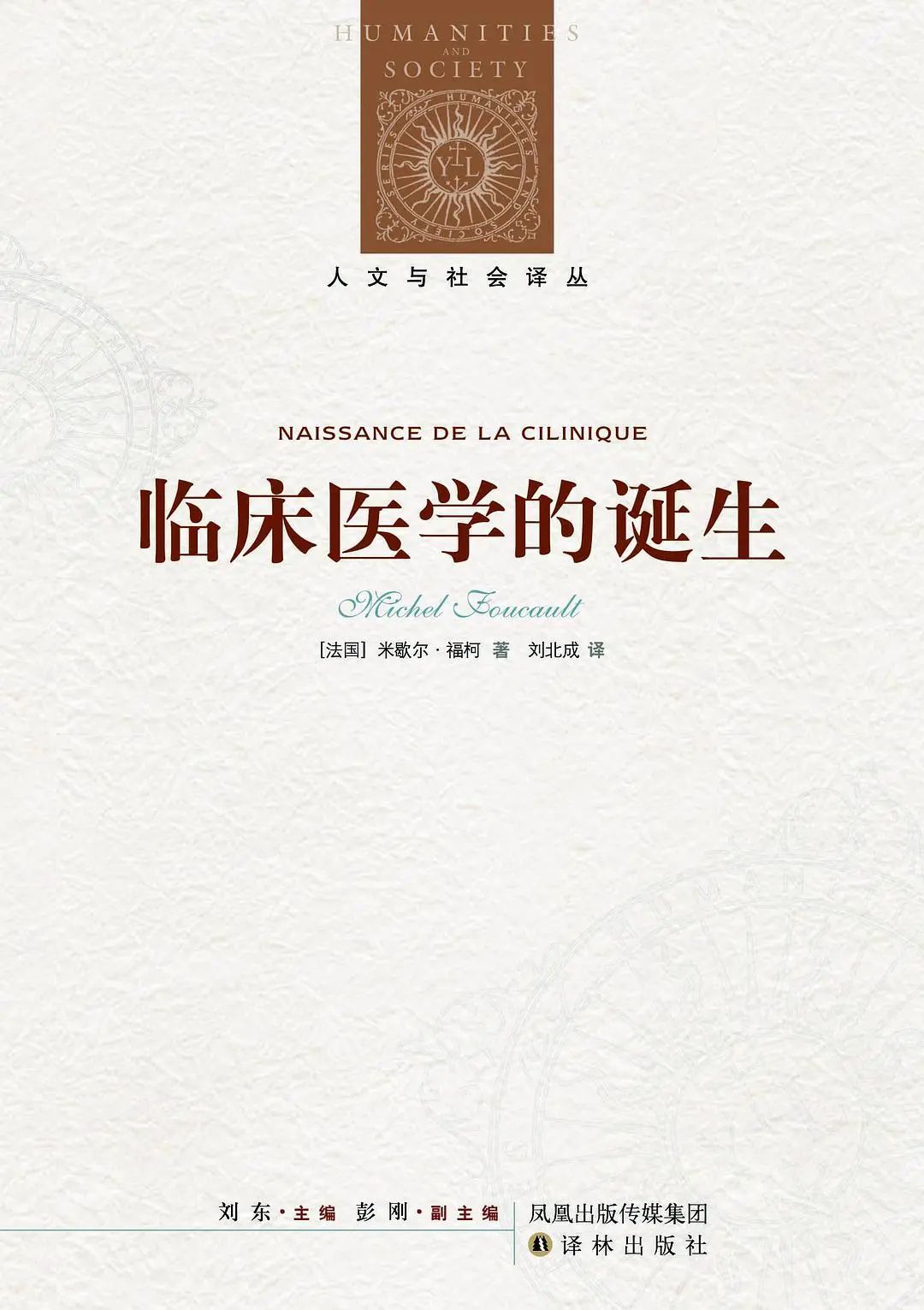
《临床医学的诞生》是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18、19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医学知识应该在病人床边形成的原则,并不是起源于十八世纪末。医学里的许多革命,即使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在这种临床经验的名义下进行的,以这种经验作为主要资源和固定规范。但是,决定这种经验的栅网本身却在不断地变化——这种栅网决定了如何获得这种经验,如何把经验接合成可分析的因素,如何找到一种话语程式。不仅疾病的名称,症状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应用于病人身体的基本感知符码,观察对象的领域,医生目视所穿越的人体表面和深层,这种目视的整个指向体系也发生变化。
自十八世纪起,医学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总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病人床边一直有恒久而坚实的经验的位置。这种经验不同于理论和体系,因为理论和体系始终变动不居,用它们的种种思辨掩盖了临床现象的纯粹性。这种理论性被认为是造成持续变化的因素,医学知识的各种历史变异的出发点,各种冲突与衰亡的场所;医学知识正是用这种理论因素掩饰了自己脆弱的相对性。相反,临床经验被认为是促成医学知识正向积累的因素;正是这种对病人的经常目视,这种历久弥新的关注,使得医学不会因出现一种新的思考而全盘作废,而是能够在其喧嚣的历史情节层次之下保存下来,逐渐地呈现出一种明确的真理形象,这种真理即使不是彻底的,至少也是发展的,具有持续的历史性。人们通常认为,在临床经验的恒定性中,医学把真理与时间联系在一起。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医学史就是借助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拼凑而成。据说,正是在临床经验中,医学发现自身的可能起源。在人类之初,在有各种虚妄的信仰、各种体系之前,医学完全是病痛和治疗方法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这种关系属于本能与感觉,而还谈不上经验;它是由个人针对自身而确立的,尚未进入社会网络:“病人凭感觉知道哪一种姿势使他舒服些或更难受”。健康人能够观察到这种无须知识的介入就建立起来的关系;而这种观察本身并不是进一步认识的契机;它也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它是自发而盲目的:“在此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我们:凝视自然”;它会自行衍生,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从而变成一般的意识形式,每一个人都同时成为这种意识的主体和对象:“所有的人毫无区别地运用着这种医学……每个人的经验都传递给别人……这种认识从父辈传给子孙”。在成为一种知识以前,临床经验是人类与自身的一种普遍关系:那是医学的极乐时代。当人类懂得书写和秘密之后,衰败就开始了,即这种知识被一个特权集团所瓜分,目视与言说之间那种既无障碍又无限制的直接关系也瓦解了:人们所了解的东西一旦经由知识秘传方式来传递,就再也不能交流给别人,也颠倒了实践用途。
毫无疑问,医学经验在很长时间里依然是开放的,并成功地维持了看(voir)与知(savoir) 之间的平衡,从而使自已免于错误:“在遥远的时代,医术是在其对象在场的时候传授,年轻人是在病人床边学习医学”;病人经常被收容在医生自己的家里,学徒随着老师从早到晚巡视病人。希波克拉底似乎是这种平衡状态的最后一位证人和最暖昧的代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医学似乎不过是这种普遍而直接的临床经验的符码化汇总;它构成了最早的总体意识,在这种意义上,它看上去与原始经验一样“简朴而纯粹”;但是由于它为了“方便其学习”和“缩短学习时间”而把这种经验组织成一个体系,因此在医学经验里便引进了一个新的维度:这是一种知识的维度,因为这种知识本身不包括目视,因此可以名副其实地说它是盲目的。这种不具有观看功能的认识乃是造成各种错觉的根源:一种任由形而上学作祟的医学可以大行其道:“在希波克拉底把医学简化成一个体系之后,观察就被抛弃了,而哲学则被引入医学”。
这犹如一次重大的日食,由此开始了各种体系的漫长历史,其中充斥着“众多流派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一历史不断地否定自己,在时间流逝中只留下破坏的印记。但是,在这种破坏性历史的下面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历史,后者更接近于自己的真实起源,因而也更忠实于时间。这种历史是由临床医学的无声生命悄然汇合而成。临床医学始终潜藏在各种“思辨理论”之下,维持着医学实践与知觉世界的联系,维持着医学实践对真理的现实画面的开放:“总是有一些医生会借助于头脑中自然产生的分析方法,从病人的外表推断出能够说明病人特异体质的资料,他们会仅限于对症状进行研究……”。临床医学是不流动的,却总是更贴近事物,因此它使医学获得真正的历史运动,它不断地消除各种体系,而与这些体系相矛盾的经验积累着它的真理。因此可以发现一种富有成效的连续性,从而保证病理学“在多少世纪里具有不中断的科学统一性”。体系与否定性时间结缘,相反,临床医学是肯定性时间的知识。因此,它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有待于被发现:它早已与最初的医学形式一起存在了;它建构了自身的丰富性;因此需要做的仅仅是,否定那些否定它的东西,推毁对于它来说毫无意义的东西,即各种体系的“威望”,让它最终“享有其充分的权利”。那时医学就能达到其真理的水平。

评论(0)